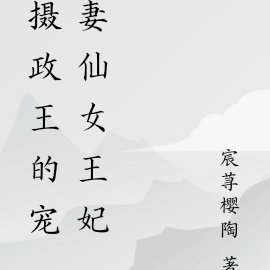前者是明知此舉‘開銷’甚大有意縱容,事後又怕被輿論報道找上門,是以提前說些冠冕堂皇‘堂而皇之’的大話打針預預防大公無私的狗腿子們,後者則不明‘世道’涉世未深,是以被前者忽悠後還搖旗吶喊自以為是。殊不知自己的親朋好友正飽受那已經上市大半月生產日期還遙遙無期的‘穿越’鎮定劑‘鎮神定精’
為了繼續忽悠他們充當節省醫藥費的‘釘子戶’,在一個‘月不黑,風不高’沒有一絲詭異神秘環境描寫可襯托心情的昏暗中午,我悄悄撥通了李秘書的電話,又一次揮霍了死人的鈔票,輕而易舉如願以償來到了佛前。
我看著佛,虔誠無比地看著。
佛卻瞪著我,目不轉睛也不斜視地瞪著我,還衝我微笑。
“佛弟子”面無表情!
我雲淡風輕。
佛繼續瞪著我,我發現它除了瞪著我,還瞪著我的口袋,我笑了。
我明白佛想來是誤解我了,便隨手示意秘書添置了些香油錢。
‘佛弟子’也笑了,道:‘施主慈悲,我佛保佑!’
我又看向佛,無比虔誠地看著。
佛卻依然瞪著我,目不轉睛也不斜視地瞪著我,還有我的口袋,衝我微笑。
我覺得自己定被佛忽悠了,想要退款,但‘佛弟子’卻堅決不撕票。
他甚是明白我的想法,微笑著道:‘施主與我佛有緣,不如將脖頸上的鸞玉借與老衲,如何?’
我差點暈倒,但想且看看他刷耍什麼把戲,反正周圍那麼多人,他想要撕票搶我玉佩倒不至於,畢竟是法制社會嘛!
想到這裡,我毫不猶豫地將青鸞玉佩從脖上取下來,讓‘臨時工’遞給他。
‘佛弟子’接過鸞玉,先是放在手中難以置信地看了看,自語道:‘施主果然與我佛有緣,但……’後半句話還沒說出,便又將鸞玉置於櫃檯上,開始唸誦經文。
我知道這‘佛弟子’定時要與我的玉佩‘開光’。由於是邱亦澤家祖傳的東西,所以我甚喜,開口道:‘開光的話,求此玉佩主人血光之災!’
‘佛弟子’笑了笑,道:‘施主,不是開光,是加持!加持!’
我想這‘佛弟子’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便想要繼續解釋,怎料他定是聽清楚了我那後半句有話,神色詫異地望著我,許久後便自言自語道:‘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何必強求一死呢?’
我瞬間明白佛弟子是誤解了我的意思,便不想再多解釋,叫‘臨時工’取了玉佩,便要離開。
離開前我看見佛衝我微笑,那笑容甚是詭異,著實捏了把冷汗,大叫著讓‘臨時工’快帶我走。
我這般舉動,愣是讓周遭誠心祈禱的信徒們狠狠地鄙視了一番,也讓我瞬間明白後來蘇榆為何寧願偷雞摸狗般與我相守,也死活不讓我們之間的戀人關係‘早見天日’
同時也對愛因斯坦曾被誤認為是瘋子的傳言深信不疑——據我薄弱到可憐的歷史知識和‘科學與迷信勢不兩立’的信條嘗試判斷:顯而易見,愛因斯坦誠然不是佛教信徒。
出來的時候,我看見天空中已經掛起了一輪驕陽,便想定是那佛祖知道了我的心意,覺得收了我的錢沒辦上什麼事情始終有失佛家的尊嚴,便把這一輪驕陽給我送來了。
在半山腰的臺階上,我們遇到了邱亦澤,將將才詛咒過他,我有點害怕,卻又不刻意躲著他。
我讓‘臨時工’推我到他跟前。
他望了望我,說:‘曉渝,你出來?’
我淡然地看著他,故意道:‘是的,下午便回學校。’
他不語,眼神裡飄過些冷漠。
我不屑一顧。
但從這似有若無的冷漠中,我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