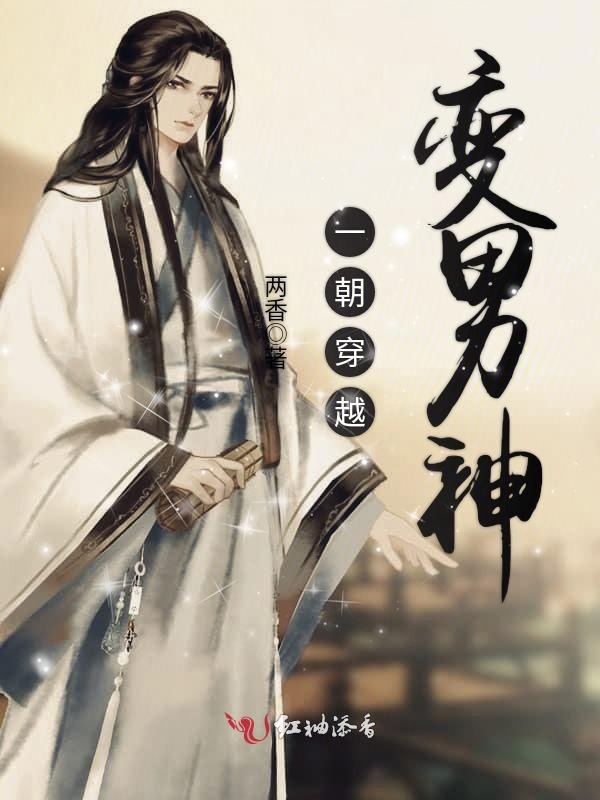州內已經連著三年遭受蝗災,六料未收,鄉村之中,十室九空,城中亦是一片蕭瑟景象。
朝廷連年賑災治蝗,依舊沒有起色。
亥時,街道上幾乎沒有燈火,只有幾處大宅中尚有燈火和歡笑之聲。
朔州知州府衙二堂內,燃著炭盆,點著燭火,照亮正襟危坐的通判鄔瑾、知州陶平、知府婁江,以及一位縣官高義。
陶知州坐在首位,婁知府與鄔瑾對坐於下首,高縣丞坐了末座。
四人皆穿常服,鄔瑾穿一領白色斕衫,頭戴唐巾,目光濯濯,陶知州端起茶盞,飲一口熱茶,笑道:“古有會稽王耀如朝霞,照亮朝堂,今日有幸,得鄔通判照亮陋室,才知古人所說不假。”
對此恭維,鄔瑾一笑了之:“敢問知州,何事星夜將我召來?”
陶知州又啜了口茶,嘆道:“高縣丞,還是你來說吧。”
“是。”高縣丞連忙起身,衝著上首三位上峰一揖。
他神色恭謹,姿態謙卑,說出來的話卻硬的邦邦響:“縣裡沒銀子、沒糧,不知是否移民就食?”
“不妥,邊關戰事連連,國庫吃緊,移民就食,是給陛下出難題,百姓也當體諒體諒上頭的難處,”陶知州看鄔瑾穩如泰山,連眉頭都沒皺一皺,只得自己皺起兩條眉毛,“鄔通判,你看呢?”
鄔瑾道:“自朔州蝗災以來,朝廷共撥付賑災銀三百萬兩,又以常平倉賑濟,蠲免一年賦稅,一石米六百文,如今漲到一千文,能買的米糧有多少,我算的清,你們也應該算的清,如此賑濟,堪比軍餉,為何就到了移民就食的地步?”
他看向婁知府:“我方才進來時,看婁知府在看小報,一定也看到了寧州市舶司上下六人被查抄一事,共計抄出白銀兩千六百萬兩。”
陶知州、婁知府本是想將高知縣的難題拋給鄔瑾,此刻聽了鄔瑾以寧州喻朔州,心頭都是一凜,後背浮出一層牛毛汗。
鄔瑾冷笑道:“二位,為何沒糧、沒錢,心中還沒有數嗎?”
高知縣今日是拼著得罪上峰,也要來求一個對策,聽到鄔瑾這般直白諷刺兩位州官,瞪大雙眼,嚥下一口唾沫,冰冷的手在一瞬間變得滾熱。
陶知州臉色難看至極,心驚之餘,一時竟然語塞,等他剛要叱罵鄔瑾時,鄔瑾卻已經起身,步入堂中,拱手一揖:“請陶知州建社倉,由諸位州官先行發動家中存慄,賑入倉內,再請富人捐糧,以此賑濟災民,度過難關。”
說罷,他抬頭看向陶知州:“蟲卵已掘,明年必定有料可收,一俊遮百醜,您說呢?”